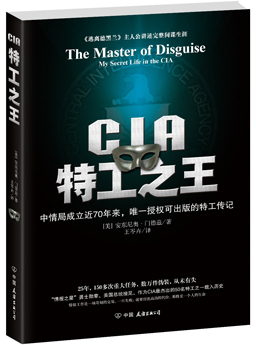
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孙子
马里兰州,蓝岭山脉,1997年8月21日
那个夏夜,焦虑又一次俘获了我,我又一次失眠了……
午夜过后,季风即将来临。机场航站楼的混凝土观景台上闷热难挡,等待的焦虑将我团团包围。透过渐渐厚重的雾霭,我费力地向楼下的停机坪张望。
从曼谷飞来的环球航空的航班已经晚点两个小时了。我看到了从沙特首都利雅得飞来的瑞士航空的航班,也看到了从曼谷飞来的德国汉莎航空的航班。一架苏联民航的IL-62 也从塔什干飞抵,缓慢滑行到观景台正下方的到港口。
突然,我的心跳加速。那架IL-62的出现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个多小时前,由于环球航空的航班持续晚点这个绝佳的理由,目标人物和他的CIA护送人员被授意原地待命。他们本该在那架IL-62着陆前离开此地,因为克格勃(KGB)的地勤人员绝不会错过这架班机。
这次行动的对象是个克格勃叛逃者。他是十天前来中央情报局寻求避难的。
此刻,他正在楼下的候机大厅等候。大厅里闷热潮湿,人头攒动。当广播里报出苏联航班飞抵的消息时,他会不会落荒而逃?
我透过霉迹斑斑的混凝土栅栏朝停机坪望去。所有的到港口前都有飞机停泊,唯独没有美国飞机的影子。这时,从曼谷飞来的环球航空波音707在暗夜中现出了身影。它着陆了,在跑道上缓慢滑行,最终停在了停机坪另一端的灯火阑珊处。
四周弥漫着浓重的雾气。精于亚洲事务的特工们管这种雾气叫“牛粪烟”。在南亚次大陆的乡下,数百万人用牛粪来烧火做饭,就会燃起这样的烟雾。我眯着眼,但环球航班的位置很难辨认。我只能等待。
从环球航班下来的乘客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跌跌撞撞地走进候机大厅。大厅里所有的厕所都人满为患,那里的潮湿和臭气立马把“牛粪烟”比下去了。我不能离开观景台。我的任务是确保目标人物和他的护送人员“雅各布”(他也是我此次行动的搭档)在环球航班停泊期间安全登机。然而,在大雾笼罩之下,我怎么才能看清他们有没有靠近飞机呢?如果我在同次航班的客流中没看见他们的身影,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入境检验口遇到了麻烦。在入境检验口,我一手操办的假证件和伪装效果将接受考验。
乘客们走出了候机大厅,朝环球航空的飞机走去,但我始终没有看到目标人物和他的护送人员。他们该不会已经逃向为逃跑准备的两辆汽车了吧?那两辆车停在停车场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动机轰鸣,随时准备疾驰而去。
无论此次的秘密行动结果如何,我都必须在楼梯下面的公用电话亭里发出信号。今晚,我们会使用带干扰的明码。“苏斯在吗?”(这意味着行动成功了。)“我可以跟乔治说话吗?”(这意味着事情出了纰漏。)接下来的计划将根据具体情况展开。
最后,我终于睡着了,神经却绷得紧紧的。即使在梦中,机场里的情景也挥之不去。我发现自己走下油漆斑驳的楼梯,挤进闷热的公用电话亭里,拿起笨重的红色塑料听筒,把一枚褐色的硬币塞进投币口,按下听筒,然后松开。没有拨号声,也没有硬币掉出来。该死的殖民地电话,大不列颠统治的遗物!很可能自从英国人卷铺盖回家后,就没人修过它了。
我再次按下听筒,硬币掉进了取币槽,我又把它塞回去。听筒里传来了嘶嘶声、咔嗒声和微弱的拨号声。我用耳朵和肩膀夹住听筒,一只手拿着酒店的火柴盒,瞥了一眼上面潦草记录的号码,另一只手迅速拨号。听筒里先是传来咔嗒声和噼啪声,然后终于传来了连贯的嘟嘟声。电话嘟嘟响着,我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四声……五声……快接电话呀,雷蒙德。十声响过,我猛地挂上了听筒。
他为什么不接电话?我看着表——3点零7分,比原定通话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我知道他安然无恙。他们在等着我发出信号。我深深吸入一口潮湿的空气,又徐徐地将它呼出,好放松双肩,缓解耳鸣。我必须打通这个电话。我又投进了一枚铜板,继续拨号。长鸣声,咔嗒声……硬币又一次落入取币槽。电话没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