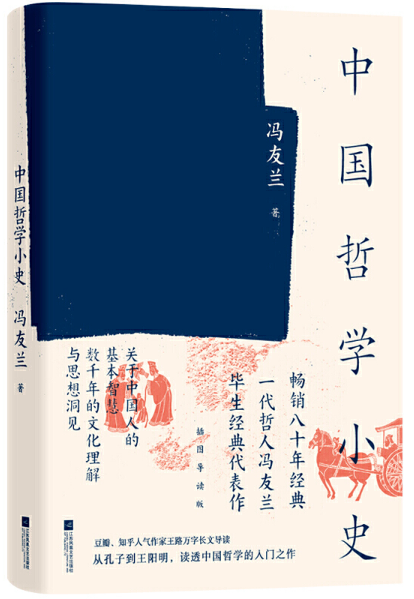
作者:冯友兰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上市日期:2020年04月
内容简介:
《中国哲学小史》是为中国哲学史奠定基础框架、指明方向的一部精华之作,通过接纳和吸收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方法,冯友兰从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切入,系统地研究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以及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宋明道学家的哲学思想,简洁而深刻,生动而详实。
此书为插图导读版,有趣的哲人形象,轻松的阅读指南,与冯友兰毕生的哲学思想一起跃然纸上。
冯友兰
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人,新儒学三大家之一。其一生的事业可概括为两句话: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中国传统社会起源时代远在基督纪元以前,它继续存在,没有根本改变,直至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崩溃,这是由于通常所说的西方侵略东方,其实是现代社会侵略中世纪社会。现代社会的根本因素是工业化经济。使用机器,使前工业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前工业经济可以是农业经济,如中国经济,也可以是商业经济,如希腊经济、英国经济。旧经济必须让位于新经济,旧社会结构亦然。看到有人对于历史,甚至对于当代事件,多么极度地无知,这是惊人的。欧洲生活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并还在经历着改变,这些改变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但同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在亚洲,西方人却倾向于称之为西方侵略东方。 现代工业主义正在破坏传统的中国家族制度,又从而破坏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工厂做工,其中在一起的人既非兄弟又非老表。以前他们依附于土地,但现在他们活动多了。以前他们与父兄一起集体耕种他们的土地,所以没有他们可以称作他们自己的产品。现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收入,以工资形式在工厂领取。以前他们通常与父母,还可能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现在他们独自生活,或与老婆孩子一起生活。在观念形态上,这在中国被名为“个人从家族解放出来”。 近年来对于孝道和传统家族制度的攻击已经少多了。这个事实的意义,不是说它们失去的影响又大有恢复,而毋宁是说它们已经几乎完全丧失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地位。用个中国的说法,它们都是死老虎,打死老虎不算英雄好汉。我记得很清楚,我年轻时,常听人辩论传统家族制度的利弊。但现在它不复成为辩论的问题。人们认识到,他们根本不可能保持它,即使他们想保持也不可能。 工业制度下的社会是在比血缘关系宽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这个制度下,个人对家族的责任少了,而对于社会全体的责任则多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服从父母的义务少了,而服从政府的义务则多了。他很少义务资助其兄弟和族人;但受很大压力,以所得税和社区福利基金的形式付出,资助社会整体的需要。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按照传统的社会理论,广义的家虽可无限扩大,但个人对家的责任并非没有固定极限。在极限之内,责任大小仍有差等。这都表现在所谓“丧服”上。按照这个制度,一个人的父母死了,必须穿丧服三年(实际是二十五个月),称为第一等的丧服。祖父母死了,他要穿丧服一年,称为第二等的丧服。在理论上,一个人的高祖的父母死了就不穿丧服,即使他们长寿见到玄孙的儿子。这说明,一个人作为一家之子的义务有个极限,它只包括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曾祖父母和他的髙祖父母。 如此按照传统的社会理论,每个个人是个中心,从这个中心向四方辐射出关系:向上是他与其父及祖先的关系;向下是他与其子及后人的关系;向左向右是他与其兄弟及堂兄弟等等的关系。James Legger的《礼记》译本,有几张图表说明这一点。在这辐射圈内,有着轻重不等的亲情和责任。中心的人视圈外的人为“亲毕”,而以朋友关系为基础对待之。
由于社会结构的这种改变,很自然地,曾是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础的孝道,必将遭到极端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在中国已经确实发生了。这种攻击在民国初年达到高峰,民国建立于一九一二年,当时就实际废除了“忠君”的道德原则。如我们即将看出的,“忠”和“孝”,过去是平行的道德原则。孝,曾被视为一切道德的善的根本,现在则被一些批判家视为万恶之源。有一本道教通俗读物上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民国初年有一位著作家套用这句话说“万恶孝为首”,虽然他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至于说“百善淫为先”。
对于传统家族制度的攻击,与其性质一致,一直是大有争议的。其结果,有些批判对它亦失于未能持平。举例来说,在许多批判中,主要的一个是说,在传统家族制度中,个人完全丧失其个性。他对家族的义务和责任如此之多,似乎他只是父母之子、祖先之孙,惟独不是他自己。
要回答这个批判,则可以说,个人就其是社会一员而论,必须对社会承担某种责任。承担责任与丧失人格并不是一回事。更何况,成为问题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内,个人对于家族和社会的责任负担,比现代工业社会内个人的责任负担,是不是真正大一些?
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家庭不过是许多社会机构之一。但在传统的中国,家在广义上实际就是社会。在传统的中国,个人对其大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际上就是个人对其现代意义的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再加上对其国家或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由于是这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的结合,所以个人对于其家的义务和责任就显得沉重了。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哲学涉及的范围内,重点在于个人。正是个人,或是父,或是子;或是夫,或是妻。正是由于或成为父,或成为子,或成为夫,或成为妻,个人才使自己加入社会为一员;也正是由于这种加入,人才使自己区別于禽兽。人事父事君,并不丧失人格。相反,只有在事父事君中,他的人格才有最充分的发展。
一个人的儿子死了,要穿丧服一年;孙子、曾孙、玄孙死了,穿丧服的期限越来越短。玄孙的儿子死了,他不穿任何丧服,即使他长寿及见其玄孙之子之死。这说明,他作为一家之父的责任有个极限,它只包括其子、孙、曾孙、玄孙。
一个人的兄弟死了,他要穿丧服一年;他的堂兄弟死了,从兄弟死了,叔伯高祖的玄孙死了,他穿丧服的期限越来越短。这说明,他作为一家之兄弟的责任有个极限,它包括的不超过其高祖的后人。
如此按照传统的社会理论,每个个人是一个社会圆的圆心,社会圆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他是一个人,也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不论中国传统社会及其家族制度功过如何,要说其中没有个人人格的地位则是完全错误的。
我提出这些辩论,只是表明,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根本不同,它也不像某些批判它的人可能设想的那样毫无道理。我说这些,决无意支持它作为今日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为了生存于当今世界,其地位无愧于她的过去,中国必须工业化。一旦有了工业化,就没有传统家族制度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地位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对它们,及其观念基础,试作同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