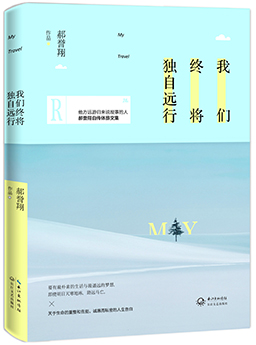
作者:郝誉翔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市日期:2016年05月
内容简介:
走得越远越热爱生活,找到内心的归宁和自处。
从繁华的世界中心到荒芜的尽头,从无声的天涯到寂静的海角,穿越年月,风尘满面,只为一些绝世的光亮、一些心灵纯净的人,一些此生不做就再也无法完成的事。
这本书里有温热的风景、他方的故事、难忘的人事,没有矫情的叙述,沉稳中清新自然。向世界的深处进发,不是为了去更远的地方,见更多的人,而是走向自己内心的深处,在孤独中体会一些圆满的真意。
跨越世界的千山暮雪,路过人世的桃红梨白,我们终将独自远行。用一段随心所欲的时光跋涉内心,让沿途的风景洗涤未知的苦涩,终其一生,与自己没有矛盾而温柔地相爱。
郝誉翔
台湾知名女作家,作品曾获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奖、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时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华航旅行文学奖、新闻局优良电影剧本奖等。
书中记录的是她从二十二岁独自一人,提着行李勇闯他乡的经历。她爬过世界脊梁,到过国境边缘无人的险峻之地,站在陡峭锐利、寸草不生的峰顶,感悟八方空境,无声涅槃;她行走于世界丰盛角落,攀登天涯,流浪海角,在红砖道上与陌生人擦肩而过,在纽约第五大道和达斯汀·霍夫曼撞个满怀,在印尼安汶岛听放学后孩子们的美妙歌声……它们是生活所遗留下来最真切的素材,是片断零碎却经年不能忘却的记忆之歌。
当喧嚣散去,岁月的光芒终将照见那一个个流浪他方的“我们”:热气腾腾地爱着、活着,兴味盎然地行走在世上的某个角落,美丽、哀愁,却朝气蓬勃并且迷人。
关于生命的重整和告别,诚恳而私密的人生告白
他方远游归来说故事的人 郝誉翔 自传体旅文集
精良图文装帧,创意翻折工艺,舒适阅读体验
只身一人,如何行走在世界的边境,与不同的灵魂碰撞?作为一个旅人,郝誉翔从未停止跋涉。她返回山东寻故乡的根;在繁荣的纽约看见小人物心中的“美国梦”;在世界边陲的西藏、不丹看见纯朴善良的眼神;在印度拉达克的寺庙,撞见独自修行的僧侣;为了潜水学习驾驶帆船,在海上摇晃一如梦游之人。
她以温柔而敏感的眼睛,看待种种遗落的美好;她笔下没有人事纷扰的躁动与喧嚣,没有独自旅行的不安与恐惧;她持续走着,将沿路遇见的故事一一记下,回来以后,再次忆起,过往不仅成为心中美丽的风景,也成为未曾遇见的自己。
这不是一本旅游书,可是书中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扉页,每一则故事、每一位她在异乡所遇见的人,都会唤起你我心里深处、为了旅行而出走的渴望,并到天涯海角,告诉他方之人:“你的生活是我远道而来的风景。”
和抢匪结成好友
据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是世界上治安最差的地方。我启程前,辗转听说有位台商朋友,在莫尔兹比港天天被同一个抢匪抢劫,抢久了,两人也居然因此熟识,从此变成了好朋友。
听了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我从新加坡登上飞往巴布亚的飞机后,便发现气氛果真不太对劲。飞机上绝大多数是巴布亚人,而且几乎清一色是男人,只有我们是极为少数的外来旅客,因此显得特别抢眼。从机首到机尾,巴布亚人没有一个不瞪大眼睛,直盯着我们瞧,赤裸裸地一点也不懂得避讳。
我很少有如此被人直视的经验,忽然想起了在纽约地铁,除非是想挨揍,否则大家都学会了两眼放空,谁也不会多看谁一眼,倒和巴布亚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本以为是飞机上空间狭小,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没想到,下了飞机,来到莫尔兹比港城市的街头,却发现满街都是黑压压的人,或是蹲,或是坐,或是站,凡是看到我们的车经过,都好奇地睁大了双眼,甚至纷纷伸出手,朝我们挥舞起来。
我很诧异他们居然如此热情,所以怎么能够不回礼呢?只好摇下车窗,不停地向沿路的巴布亚人微笑挥手,而那种盛况大约可比拟英国女皇出巡,手挥久了,也不由感到一阵轻飘飘的虚荣。
但巴布亚人的好奇心还不只如此。我在街上看到巴布亚小孩,长得天真可爱,便忍不住想和他拍照,没想到小孩不仅不拒绝,我们才把相机一举起来,就忽然四面八方不知打哪儿涌出来许许多多的孩子,大大小小,男女皆有,全都高声欢呼着,飞奔过来一起入镜。有的孩子伸手抱住我的腰,有的紧搂我的肩膀,有的还握住我的手,和我十指牢牢得紧扣。他们做得如此自然而然,全无冒犯之意,而一个个孩子面对相机镜头,全都笑得咧开了大嘴。
我从没在别的国度遇见如此活泼的孩子。
显然巴布亚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我们有不同丈量的标准。肢体的亲密接触,或是彼此之间的眼神交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当中,而不需要任何的防备或隔阂。相形之下我们却是恰恰相反,一与人靠近,直觉便是立刻撇过头去,抽出手指,或者干脆赶紧往后退一大步。
我们是为了潜水而去,所以只在莫尔兹比港停留一上午,接下来,都将会住在船上。导游这趟短暂城市之旅的,是当地人Andrew,典型的巴布亚长相,皮肤深黑色,头发蜷曲,笑的时候露出一口雪亮的大白牙。或许是旅游业在当地实在不发达,Andrew看到我们一行人,居然害羞得手足无措,紧张地一直望向窗外。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害羞的导游,或许只是一个新手吧,大家心里嘀咕着,只好鼓励他开口,介绍一下自己的国度。
Andrew迟疑了半晌,害羞地微笑起来,仿佛小学生走上讲台,终于鼓足勇气开始说:“在巴布亚,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所以在这个城市中,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顾客,还要多上许多……”说到这里,他竟然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仿佛这是全天下最可笑的一件事。
哪有导游这样介绍自己的国家呀?仿佛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似的。接下来,他滔滔不绝,边说边笑,说这儿有兴盛的伐木业、咖啡种植、棕榈油工厂等等,可是,老百姓却一点也没有受惠,因为外国人跑到巴布亚砍木头,把树林铲平,制成家具,然后再以贵得离谱的价格,卖回给这里的居民,还来此炒作房价,使得当地人穷无立锥之地……
“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公平。”Andrew讲到这里,再三重复着,然而他边抱怨,脸上却还边洋溢出十足的喜感。
难怪贾德·戴蒙(Jared Mason Diamond)在《大崩坏》(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一书中,赞美巴布亚人是世界上最具有好奇心的民族。而诺曼·路易斯(Norman Lewis)在《东方王朝》(An Empire of the East : Travels in Indonesia)也盛赞在巴布亚人的文化之中,没有杀戮,因为这儿得天独厚,不论海洋或山林,皆拥有天然丰富的物质资源,这使得争夺成为一件不必要的事。而这或许也说明了巴布亚人的乐观信心,究竟是从何得来的?他们仿佛与生俱来一种强大的包容力,即使在面对白人的殖民,或是外来的经济侵略之时,都还能表现出特殊的幽默喜感。
直到如今,这种乐观的基因,似乎还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即使曾经吃过不少白人殖民者的亏,即使如今巴布亚的经济命脉,也大多掌握在澳洲甚至中国商人手中。社会资源严重分配不均,导致巴布亚的物价飙涨,失业率高达八成,满街都是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者。他们蹲坐在人行道上发呆,而那副姿势仿佛和生活在丛林里时,仍旧一模一样,而一整天的光阴就在发呆、沉思和默想之中,一点一滴地度过了。
在他们的身上,竟还残留着丛林生活的印记──那是他们的祖先最常做的事情:坐在树下发呆、乘凉、看海、捉蚊虫,或是采集热带树林中丰饶的树叶、花卉、果实,拔取禽鸟的羽毛,好来装饰自己裸露的身体。他们的姿势不变,只是这一回,背景却从绿色雨林变成了水泥大楼,从林中的鸟兽,变成了街上呼啸而过的汽车。
我总觉得这幅画面古怪异常,他们是被错置在摩登时代的部落人。后来,我也学会了大胆迎接他们的注视,并且在里面看见了我们被文明所规范化之后,所削落掉的另一半灵魂。也或许我非常幸运,在莫尔兹比港始终没有遇到抢匪,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结成好友。不过,当我在街头拍照时,却常不知不觉引来一堆好奇的巴布亚人,像是强大的磁铁一般,把整条街的人全都朝我这儿聚拢。弄得我最后只能抱着相机,边笑边落荒而逃,留下一街巴布亚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
然而当他们站到我身旁,自然而然便和我亲昵地十指交扣之时,我不禁想,如果真要和巴布亚的抢匪结成好友,也是不无可能的事啊。
月亮的眼泪
我喜欢坐船,却也晕船。
潜水时,常在船上住好几天,我却总是住到不想下来。我总爱站在甲板前方的尖端处,抓稳栏杆远眺,在那一刻,放眼所及唯有海,在前方无尽晃荡。如此纯粹,如此辽阔自由,而我竟可以连续注视海面一个下午,也不感到无聊。时间既久,晕成了常态,便也就不再晕了。
因此许多人喜欢豪华邮轮,平稳又奢华,但我习于晕浪之后,更偏爱的却是那种只适合二十人以下乘坐的,顶多只有六、 七个舱房的小船。房间小得仅容转身,床铺是上下舖,而且厕所还得全船的人共用。船只的维修不易,漏水、断电,或是夜半有不明物体在发间爬行,都是我的亲身经验。然而它的好处是除了睡觉以外,没有人会想要关在房间里,大家自然而然聚到甲板上,看书、聊天、发呆、沉思、看海,无所事事晒太阳。
又因船身很小,所以不论是潜水客或是当地的船员、船长,多半一起吃饭、休息、生活,格外亲密。我去马来西亚西巴丹(Sipadan)潜水时,便住在这样的小船。船员都是马来人,夜晚大家聚在甲板乘凉,拿出吉他轮番唱歌,一边说笑打闹。这群大海的子民似乎特别天真开朗,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却也不禁跟着开怀大笑。
当我倚在栏杆上吹风时,一个瘦瘦小小,被太阳晒得乌黑的船员,忽然站到我身边,害羞地微笑着。他口中缺了两颗门牙,咿咿啊啊地对我比手画脚,又反复指着自己的耳朵,摇摇手。他说了好久,我才弄懂他的意思,原来他的一双耳朵几乎聋了。
他又试图用手势告诉我,他的故事。我猜测,他小时候去潜水抓鱼,或许是因为渔民炸鱼,也或许是因为耳压平衡没做好,总之在一瞬间,他成了聋子。他看我仿佛是懂了,便沉默下来,望向黝黑的海洋和远方忽明忽灭的渔火,然而他的脸上却始终是微笑的。
这些在船上偶然邂逅的异国人们,让我读到了更多关于海的故事。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潜水时,我们的船长是德国人,在那一带经营潜水旅馆和船只。他的身世也非常特别,因为父亲是植物学家,所以他在所罗门群岛出生长大,跟随父亲在这一带进行田野调查。他后来爱上潜水,成了知名的潜水家,出过书,也发现了不少新的潜点和生物。他结过婚又离婚,有两个女儿,巴布亚有两座珊瑚礁群,便是以他女儿的名字来命名。趁着潜水的空档,德国船长教我如何驾船、放锚,全是透过电脑卫星导航系统,只要轻旋一颗黑色的转钮即可。
“就这么简单吗?和我想象中的驾船差很多啊。”我依他指示把锚放下、定泊,有点吃惊。船长笑了笑,便调整成以轮舵来驾驶,好让我过一下掌舵的瘾。
这船长简直像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逃离西方文明,来到了世界边陲的边陲。但这儿虽然偏远,海底景观却也更为美丽,或许是因为附近盖了棕榈油工厂的缘故。“不过,这只是‘或许’喔。”船长再三强调。
即便原始如巴布亚,也都逃不了敏感的环保议题,而现代化的斫伤,更是无所不在。船员S告诉我的,是故事的另一面貌。S是道地巴布亚人,友善活泼,四十岁了,却仍未婚。我讶异他如此晚婚,S却表示他一心想娶外国女人,好离开这个地方,他甚至问我台湾女人是否可以嫁外国人?我有些尴尬,赶紧转移话题:“为什么要离开呢?这儿是如此的美丽。”
“我已经厌倦潜水了。”S摊开双手,坦白回答。
在他的眼中,这些远道而来的潜水客必定像是一群傻瓜。然而S说,因为长期潜入深海探勘,他的体内已经布满气泡,然而船长却又逼迫他非潜不可,枉顾他的健康……。
在澳洲,也曾发生过类似状况,许多原住民被绑架,强迫潜入险恶的海域中摘采珍珠,导致他们相继死去,而从此,珍珠便以“月亮的眼泪”闻名。于是当S又再度戴上面镜、背着气瓶,下海去帮我们探测潜点的状况时,我眼看他的身影没入湛蓝的海水中,不禁涌起了一阵无言的难堪。
贾德·戴蒙在《大崩坏》中,大力赞美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社会经营典范,适应环境能力也最强,所以他们最终是否能够否极泰来呢?我不知道。不过,S到底是从海里回来了。不管如何,我们现在都是置身在同一条船上,而将我们轻轻托起的,便是无边无际的美丽汪洋,那轻柔的浪尖如碎钻,如珍珠,如眼泪,正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因为楚浮,非常法国
二十出头年纪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楚浮(Franois Truffaut)。
每当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从台大研究生宿舍走出来,沿着罗斯福路的红砖道走着,去搭公车,然后便随车晃啊晃,抵达太阳系MTV。坐在公车上,车窗哐啷啷的震动,震到人头皮发麻,但现在的我却好怀念那时公车如何在颠簸的路面上弹跳,整个人几乎要从座位上飞了出去,而怀里却还紧紧抱着圣玛丽刚出炉的法国面包,暖洋洋的,一路上闻着面包的香气,克制自己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因为要留着待会儿躲在MTV的黑暗包厢里,一口一口搭配着楚浮。
那便是年轻时最奢华的一顿飨宴了。但彼时台北的下午,不知为什么总是冷冷清清的,街道空旷,只剩下落了一地的枯叶,以及白色的纸张在柏油路面上打滚,让人误以为莫非是新年的假期到了。然而,那种冷冷清清毕竟是午后的一场错觉罢了,就好像楚浮,也总是让我产生永远都是夏日的错觉一样。
喜欢楚浮,说不出理由。
他不像侯麦(Eric Rohmer)老是喋喋不休;不像高达(Jean-Luc Godard),真是聪明又深奥;也不像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把文明、道德和经典拿来拆解颠覆;更不像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国族、政治、寓言的企图多么深邃庞大。这些导演的电影,适合留到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观赏,然而楚浮的电影却是属于年轻人的。看了楚浮,我们会忍不住站起来,想要去模仿,模仿电影里的人在风中飞也似的用力骑脚踏车,大笑,做鬼脸,摇晃脑袋,像只机灵的小鸟一般轻盈地唱歌,或是住在一间白色的房子里,打开门,跑出来,在发光的草地上打滚,然后捧起对方的脸疯狂亲吻,或是嘴巴咬着烟,绕房间行走,假装自己仿佛是一列噗噗响的蒸汽火车。
因为楚浮,二十出头岁的我们非常法国,心目中美女的典范,才不是现在流行的日韩女星,而是《夏日之恋》(Jules & Jim)的珍妮·摩露(Jeanne Moreau)和《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的杰奎琳·比塞特(Jacqueline Bisset)。她们有着一双坚定的眼神,骄傲的嘴角,刨光木头似的修长小腿,蓬松的长发,纤细的身躯上套着宽大的毛衣,或者是一袭剪裁合宜的洋装。她们谜一般的内在性格,却要让所有不幸遇到她们的男人,都甘愿因此而受苦、疯狂。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是为了楚浮,才迷恋法国的,还是为了法国,才迷恋楚浮。但二十出头岁的我们,真的是非常法国。抠刻着把饭钱省下来,跑到和平东路的“法国工厂”买贵得吓人的海报和卡片,回来贴在每人空间不过 一坪大小的宿舍墙上。台北第一次办“法国影展”,就兴冲冲赶去排了整整四个小时以上的队伍,只为了看“IP5”。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那部电影里一大片悬浮在梦境似的绿色森林,巨大的树木,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时间仿佛多到用不完,足以让我们完全脱离现实,去编织一场法国梦。然而事实上,那时我们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不法国。公馆捷运的工地就在研究生宿舍旁边,日以继夜,不停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好像从宇宙洪荒开始就一直存在那里,没完没了似的反复,也不知道究竟在撞击些什么。
从舟山路走到罗斯福路时,我们必得要提心吊胆,一不留神,就会被工地喷得一身的泥浆。我们经常在弥漫臭气、又闷热不堪的水源市场角落,解决三餐。传说以前公馆有一条河川,四周环绕着绿色的稻田,但这听起来,却活像是一场天方夜谭。
因为穷,我必须要接下很多家教,应付各式各样的奇怪小孩,而聘请家教的家庭,竟不全然是富裕的,有的付不出家教费,到了月底,小孩的母亲只好抱歉地微笑着,从厨房中拿出三罐味全苹果奶粉,给我作为抵押。我抱着三罐奶粉,慢慢穿过暗暗的狭巷。骑楼中传出浓烈的尿骚气味,摩托车的机油流成了一滩滩黑色的血。我踮起脚尖,小心绕行,以免一个不慎,踩得满脚乌黑。但我却还总以为自己是走在楚浮的电影里的,非常之法国的轻盈,而四周围也不是浊重的黑夜,而是一个吹着凉风,树叶哗哗作响的明媚的夏天。
于是楚浮在我们的生活中矛盾地存在着。
但奇怪的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其矛盾。《夏日之恋》是反复看过很多次了,我把歌词抄录下来,照着珍妮·摩露的嘴型,唱起一字也不懂的法文歌。晚上我坐在宿舍的桌前,室友都睡着了,只剩我独自面对镜子,模仿珍妮·摩露的表情:那种抬起下巴的微笑方式,那种令人见到了以后,都不禁感到可以值得为这微笑付出一切的微笑。
直到近年,我才读到夏宇翻译的亨利·皮耶·侯歇(Henri-Pierre Roche)《居乐和隽》:《夏日之恋》的原著小说。而《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Les Deux Anglaises et le Continent)也是改编自侯歇的作品。读着读着,二十多岁的记忆又不禁啪啦啪啦地回来了,仿佛是大梦初醒一般,没有想到小说写得如此简洁有力。楚浮说:“这本小说叙述的是两个朋友与他们共同爱人之间的故事,幸亏有一种一再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他们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矛盾地温柔地相爱。”
如此温柔的爱情,虽然也被年轻时的自己不切实际的向往过,但在付诸作为时,竟又往往是充满了不堪的粗心与盲目。如今已十多年过去了,我才真正能够懂得,楚浮这段话的意思。然而可惜的是,珍妮·摩露在电影中美丽依旧,但夏天却是一去,就再也不能够复返了。
……